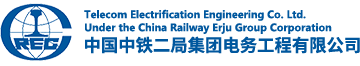
项目部的营地,固执地钉在半山腰的密林里。每到傍晚,赭红色的夕阳便从山巅掠过,接着,墨色便从四周的树林里涌出,像打翻了一壶陈年普洱。浓俨的夜色悄悄地漫过远方的山脊线,漫过还在半山坡上吃草的牛群,漫过村庄的吊脚木屋和大黄狗,最终,也将我们营地吞没了。
营地里,中老两国的工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耳边蛙鸣与虫叫此起彼伏,白日的喧闹渐渐沉入寂静。晚饭后,工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花坛边上,烟头忽明忽暗,像是男人们放牧的萤火虫。宿舍里,烟草的焦香与老挝啤酒的麦芽气息交织混合,在空气中酿成一层微醺的薄雾。 “幺儿,作业写完了没得……想不想老汉嘛……”来自四川的工人马贵洪正举着手机与上小学的女儿视频,脸上的皱纹在屏幕光里显得更深了;隔壁房间的老周则摸出半瓶包谷酒和一包花生米,与工友摆起了龙门阵;晾衣棚下,老挝工人坎佩正晾晒刚洗的工装,水滴答滴答地落下,像挂了一串沉默的风铃。
今夜轮到我巡夜值班,我持着手电筒踱步于营地,昏黄的光束扫过四周,在粗砺的地面上投下摇晃的影子。走到营地大门口,抬头望向远处,我盼望能有一台汽车驶过,车灯便可将这黑暗划破,然而,还是没有,我的眼前仍是沉沉的无边的黑暗。这时山野中蛙鸣虫叫声,也像燃尽的火苗渐渐熄灭。我关掉手电筒,静静地观察着眼前处子般鲜润的黑暗,心中竟升起一种特别的感动。
成都的夜晚,由于灯火通明已经没有黑暗可言了。那里的霓虹灯、车水马龙、人流不息,构成了一幅永不疲倦的繁华图景。而此刻,在老挝的深山里,黑暗恢复了它本真的面貌——洁净、纯粹、毫不矫饰。
营地的黑夜是干净的。没有车灯划破夜幕,没有小酒馆的喧嚣,没有烧烤摊的油烟,只有沉沉无边的黑暗,像一块未被污染的黑色丝绸,轻轻覆盖在山林之上。这黑暗不掺杂任何杂质,它只是黑暗本身,是光明的另一面。
我忽然明白,上帝制造的黑暗,原是为了让我们安眠。它不是惩罚,而是恩赐。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黑暗是一张温床,孕育着梦境;它是一方净土,滋养着思考。我们这些被繁华热闹的城市驯化太久的人,早已忘记了如何与黑暗相处。我们企图把夜晚变成了白昼的延续,用人工的光明驱赶自然的黑暗,却不知自己失去了什么。
黑白交替,本该是最朴素的哲学。光明让我们行动,黑暗让我们休憩;白昼给予我们劳作,夜晚赐予我们沉思。这简单的轮转中,蕴含着宇宙最基本的韵律。而我们却妄图打破这种平衡,用不夜城的光污染,用二十四小时的娱乐,用永不停止的消费,来否认黑暗存在的权利。
营地巡夜,让我有机会这般酣畅淋漓地感受久违的黑暗与宁静。这黑暗像一泓清水,洗去了我身上沾染的城市浮躁。我开始渴望保持这种状态,渴望在黑暗中找回那些被光明遮蔽的感知能力。
沉沉黑夜终将过去。我忽然期待起黎明来,不是城市里那种被汽车喇叭和早点叫卖声惊醒的黎明,而是山林间那种清清爽爽的黎明。当第一缕阳光穿透黑暗时,它必定是纯净的,未被污染的,如同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
黑暗与光明,本是一体两面。我们之所以能够欣赏黎明的清爽,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黑夜的纯净。在这深山营地里,我重新学会了等待——等待黑暗自然地退去,等待光明自然地降临。这种等待不是被动的,而是充满敬意的。
也许,人生亦是如此。我们需要经历黑暗,才能懂得光明的珍贵;我们需要沉入思考,才能更好地行动;我们需要休息,才能更有力地前行。营地里的黑暗教会我的,正是这种古老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