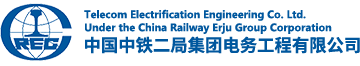
亲爱的小陈:
展信安!
许久未见,不知你近来可好?她们都说“写信是这个快节奏时代独有的浪漫”,机缘巧合之下,我也想提笔,把这份浪漫分享给你。假若你知道此刻我身处何地给你回信的话,想必会惊讶至极,因为这是你梦里梦不到的远方。
回想你给自己写的第一封信,那是一个语文晚自习,你合上《我们仨》的书页,感喟于杨绛先生“万里长梦”历历如真的凄怆,我似乎听见生死离别在十七岁的琴弦上拨响一声沉重的低音。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的慨叹久久萦绕你的心头心头,我仿佛看见世事无常的缺憾在十七岁的艳阳天落下一场淅沥沥的小雨。
可对那时的你而言,有关生死、告别和遗憾这类宏大且抽象的人生课题像是似懂非懂,故而揣着诸多疑问落笔向未来寻解。
其实你的来信我早已知悉,之所以现在才回信,是因为此前的我似乎陷入了找寻“完美答案”的怪圈,总想着写出一份漂亮的答卷。殊不知,人生的意义在于尽兴体验,那叶载着未来的小舟没有既定的轨迹,亦无法驶向你所期待的每一条河流。但无论烟波如何飘兀,你始终向前,希冀着更广阔的江海。如今,我回望过往,身后的万重高山和滂沱风雨已然镌刻着你生动鲜活的模样,这胜过所有枯燥的答案。后来的某一天,你会发现:找寻自己远比寻找答案更重要。于是,你开始乐此不疲地出发。
十八岁,你旁观着云边镇的故事:“山这边是刘十三的童年,山那边是外婆的海。这是他曾日夜相见的山和海。在遥远的城市,陌生的地方,有他未曾见过的山和海。”寥寥数语有如自由和远方的呼唤,而你也如愿抵达。
二十岁,是大胆做梦的年纪,你以为自己会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所写的那句:“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然而现实是,二十岁之后的生活不会一直浮在阳光中,成长本就意味着捶打和磨练,自然免不了被风雨侵袭。
二十一岁,举棋不定,你总是害怕迈出第一步,哪怕你明明知道“举步之际无需周全”的道理,你总会因为未来的不可预见而焦虑迷茫,哪怕你知道一切终将过去。既如此,便希望我们再勇敢一些,因为前方没有“西瓜炮”,都是“芝麻雨”。
二十二岁,一半校园,一半职场。“转变思维、拥抱成长”的忠告不绝于耳,面对众多的建议和方法论,你不断思考、变化,看法和认知也不断被推翻和重塑。我本想与你诉说这一路的跌撞起伏,但反复思量、提笔又落,原来,那些当时以为迈不过的坎和被卷入的晦暗并未留下不可淡去的痕迹。想起曾经的你总会鼓舞自己:只要一路向前,就能把昨日的难熬甩在今天身后。我恍然,确是如此。
二十三岁,你的足迹从南到北。四季轮转,你不断感受和探索着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你曾在橘子洲头眺望湘江水奔流北去,也在长白山巅俯瞰天池的纯净无瑕,在景德镇聆听千年瓷都奏响“泥与火之歌”,也在大陆东边的海滨城市追赶东升西落的太阳;终而看山、见水、寻众生、找自己。此刻的我,身处距你三千公里外的东北,先不必惊讶和疑惑,或许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带给你更多的是惊喜。你会透过车窗惊叹平原的一望无际,会在盛夏的凌晨四点看朝阳初升,也会在深冬傍晚的路灯下望着飘雪入了迷。
世界如此精彩,感谢你当初坚定地选择出发。虽然出发和离别似乎总是形影相随,但很庆幸,在往后几年的光阴里,你逐渐学会了坦然面对每一次分别,也认真学着好好告别。慢慢地,离别愁绪不再将你长久占据,告别的主色调也不再只是忧郁的蓝,你每每记录下的分别时刻,都为昨日的缤纷添上一抹亮色。你会明白,不舍和感伤是暂时的,日后天南海北、山遥水阔,或许大家会在不确定的未来再相逢。亲人也好,朋友也罢,惟愿君无论来与去,皆能飒踏如流星。
信写至此,我仍要感谢十七岁的你热烈勇敢,向着翻腾的海浪和群山尽头的落日,敢于千千万万次奔跑。你绝非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去做林间风、山涧溪,做皎皎月光憩檐尖,岁岁星子明夜色。长路漫漫,我只盼你记得为何出发。
我在未来等你。
2024年的自己